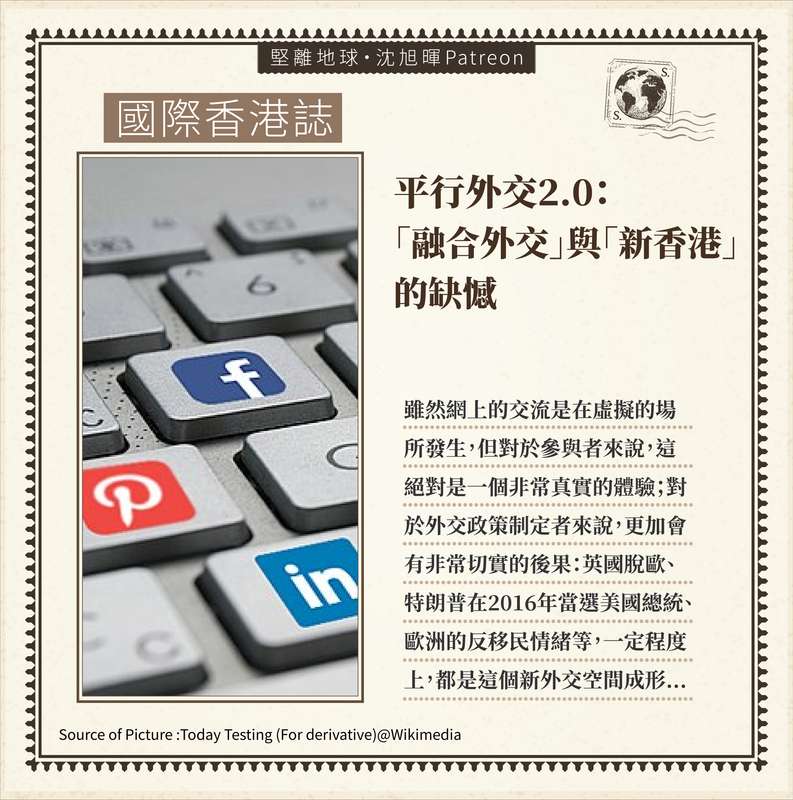【國際香港誌 104】平行外交2.0:「融合外交」與「新香港」的缺憾 (Patreon)
Content
在第二章,我們介紹過香港擁有涉外關係權限的國際關係理論基礎,例如「平行外交」、「多孔外交」等,這些理論到了互聯網年代依然實用,而且意涵更進一步。但香港因為主權移交後的特殊政治背景,卻很難與這些理論的「2.0」版本與時並進。
例如剛談及的數碼科技,的而且確可以為國家政府機構提供新的工具,去協助處理國防、外交等國家事務。但數碼科技在公共領域帶來的影響,並不是純粹線性、且單向的;國家機構運用數碼科技進行探查、倡議的同時,公眾亦會以不同方式作出回饋,互聯網某程度上正是一個揉合了公眾與數碼科技的新國際空間。
以外交為例,隨著社交媒體興起,一國外交官、或駐外官員擁有自己的個人社交媒體帳號十分平常,這些外交官能夠透過這個平台,表達自己或代表國家的看法,再加上利用個人魅力,去號召群眾,或倡導某信息,或宣傳某種意式形態。但這些都是非常理想化的想法,而通常現實是不會那麼理想的。在這個過程中,只要外交官在社交媒體上與公眾進行交流,其言論就會被放大檢示:或被批評過於激進、或被批評不適當地示弱、或被自己國民讚好、但引來外國人民不滿,不可測性隨之大增。但要是拋棄這工具,則是削足就履,就算封閉如北韓、講求傳統並殘暴如「伊斯蘭國」,亦不會如此。
在外交層面上,數碼科技不只是一個工具,還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國際互動空間,這便是學者Hocking所說的「融合外交」(integrative diplomacy)[1],或是Gregory等學者所形容的外交的「公共維度」(public dimension)[2]。在這層意義上,這個新的外交空間的構成重點,並不是單純取決於裡面個別行為體的動作,而是取決於行為體之間的交流。雖然網上的交流是在虛擬的場所發生,但對於參與者來說,這絕對是一個非常真實的體驗;對於外交政策制定者來說,更加會有非常切實的後果:英國脫歐、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、歐洲的反移民情緒等,一定程度上,都是這個新外交空間成形、「開放」後的產物。
問題是香港、特別是《港區國安法》通過後的「新香港」,雖然依然被北京期望對國際社會「唱好香港故事」,但已不能發表任何有異於中央政府的網上聲音,就連境內香港人也失去了網上暢所欲言的民間身份。結果,也就失去參與互聯網時代這種「融合外交」或「平行外交2.0」的能力,連帶香港的國際身份,也難免逐步一落千丈。
[1] Brian Hocking, Jan Melissen, Shaun Riordan and Paul Sharp, “Futures for Diplomacy: Integrative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”, Report No. 1. The Hague: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‘Clingendael’, October 2012, https://www.clingendael.nl/publication/futures-diplomacy- integrative-diplomacy-21st-century (accessed 20 March 2018).
[2] Bruce Gregory, “The Paradox of Public Diplomacy: Its Rise and ‘Demise”. Washington, D.C.: Institute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, February 2014.
▶️ 延伸視頻:譚志強:澳門對葡語國家的白手套功能,還剩下多少?(上)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uT4CK6McOi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