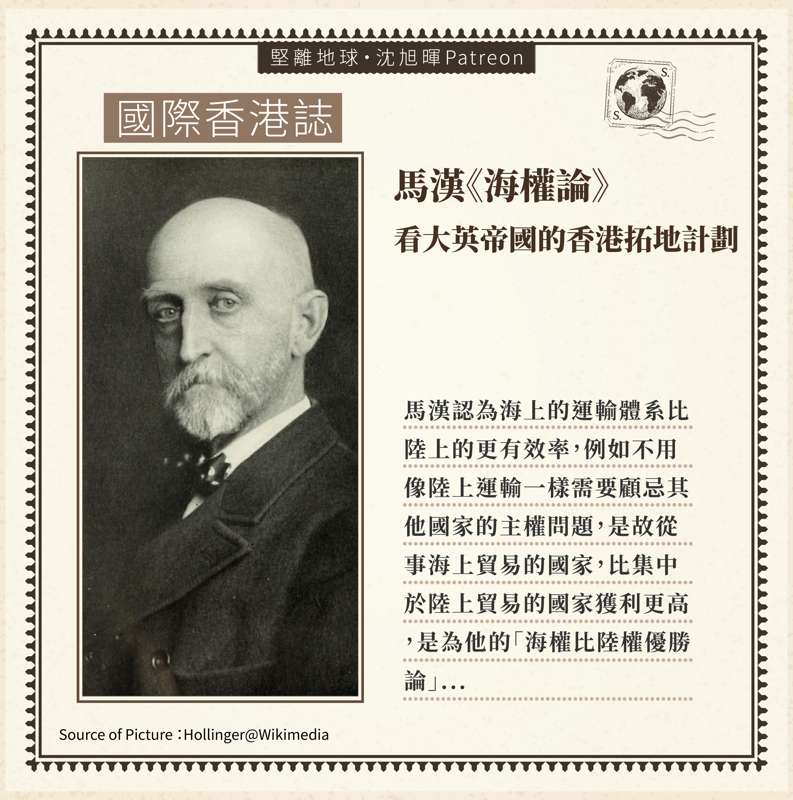【國際香港誌34】馬漢《海權論》看大英帝國的香港拓地計劃 (Patreon)
Content
從香港島、九龍半島到新界的拓地過程中,我們看到英國政府的地緣政治計算考慮,與香港各個地區的不同結構性功能。而進一步理解香港與大英帝國海洋貿易的關係,我們不妨參考美國軍事家馬漢(Alfred Thayer Mahan)的經典著作《海權論》,作為本章總結。
馬漢畢業於西點軍校,曾參與美國南北戰爭,後來成為海軍戰爭學院院長。1890年,馬漢將自己課堂的筆記整合成《海權對歷史的影響》(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) 一書,並在書中提出「海權」概念,令他後來被稱為「海權論」始祖。[1] 這書出版後一紙風行,當時的美國、英國等大國,均深受海權論啟發,乃至對一戰爆發、之後的《華盛頓軍備協議》,均有直接影響。《海權對歷史的影響》闡述了從十七世紀中葉的帆船年代,到十八世紀後半葉美國獨立戰爭完結後的世界軍事史,馬漢認為「海權」這概念,能夠有效解釋一個霸權能否持續保持興盛;大英帝國對香港的拓地,亦深諳其道。
在書中,馬漢指出英國之所以能贏得歐洲大陸的七年戰爭(1756-1763),全賴英國在戰前成功透過海洋獲得大量財富(所謂「海權」,就是透過海洋創造財富)。國家能透過船隊,將商品運到世界各地並藉此獲利,有利益固然會引來競爭,所以又有「制海權」之說,即強調國家不但要從事海上貿易,還要確保船隻安全,甚至主動擊退其他對手,成為海上霸主就能獨佔利潤。馬漢認為海上的運輸體系比陸上的更有效率,例如不用像陸上運輸一樣需要顧忌其他國家的主權問題,是故從事海上貿易的國家,比集中於陸上貿易的國家獲利更高,是為他的「海權比陸權優勝論」。英國與大清帝國的戰爭源起,與經營香港殖民地的動機,全在於此。
在書中引論,馬漢開宗明義指出海洋與商業和軍事的連結。海洋商業的優勢,在於水路行進比陸路容易及便宜,尤其在陸路交通建設落後、或處於持續的戰亂時期,海上交通相對更為安全快捷。基於這種優勢,海上商業對於國家的財富及實力影響深遠,國家必然會盡力排斥其他競爭者,以獲得更多好處,而對應因此衍生的衝突,正是建立海洋軍事力量的目標。無論是否處於戰爭時期,透過佔據具戰略意義的海岸據點,滲透不同海域的要衝,將可以支撐國家的海上力量。海岸據點可以為遠行船隻提供必要時的避難場所,同時提供補給。在香港拓地這歷史案例中,《南京條約》割讓香港島的條文,即提及修理船隻及儲存供給物資等作用。
此外,馬漢認為海岸據點的關鍵,能夠體現在生產、航運及殖民地三方面;而基於生產從而衍生商業活動,為設立香港這類海岸據點,提供了最大誘因。香港開埠初期雖然沒有太多本土生產,但卻是貨物進出中國大陸的重要門戶,因而成為了世上最繁忙的自由港之一。及至二十世紀五○年代後,香港依靠廉價卻勤勞的勞動力,加上來自歐美的資本,發展出龐大的製造業,展現了本土經濟發展的另一種面向,反映香港這國際港口依然服膺於海權論的運作倫理之內。
至於航運,指的是支持海上貿易的航道及運輸事業。南海的航運網絡發展,可以追溯至早於七至十四世紀的蘇門答臘王國、十五世紀的馬六甲蘇丹王朝等,而東海則有著十五世紀的琉球王國與中日兩國的貿易連繫,後來都成為歐洲殖民帝國染指道的頭號目標。基於亞洲內部原有的海洋網絡並加以發展,歐洲勢力參與其中,並得以擴大海上勢力,這正是香港崛起的宏觀背景。例如香港開埠後不久的1843年,英國「半島東方輪船公司」就在香港設立分公司,開闢歐洲至遠東的航線,同時經營香港與廣州及其他口岸的航線,就是航運之於大英帝國重要性的彰顯。
至於馬漢眼中殖民地的意義,絕非中國等國家官方宣傳的掠奪行為,而是主要在於建立安全區以保護商業發展,同時擴大航運活動,這和強調直接侵略和奪取資源的老殖民主義有根本差異。在鴉片戰爭前後,英國海軍利用香港作為基地,突破大清帝國海防、並成功侵入內河及運河系統,其目標之一,正是保護自由貿易的進行,這概念當然有其爭議,但卻是香港存在價值的支點。其後於1920年代末的中國北伐戰爭、國民黨清黨和日本前期滋擾邊境等戰事期間,英軍亦透過香港運輸兵源至上海,以保護多國共管的上海國際租界。
[1] Alfred Mahon,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, 189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