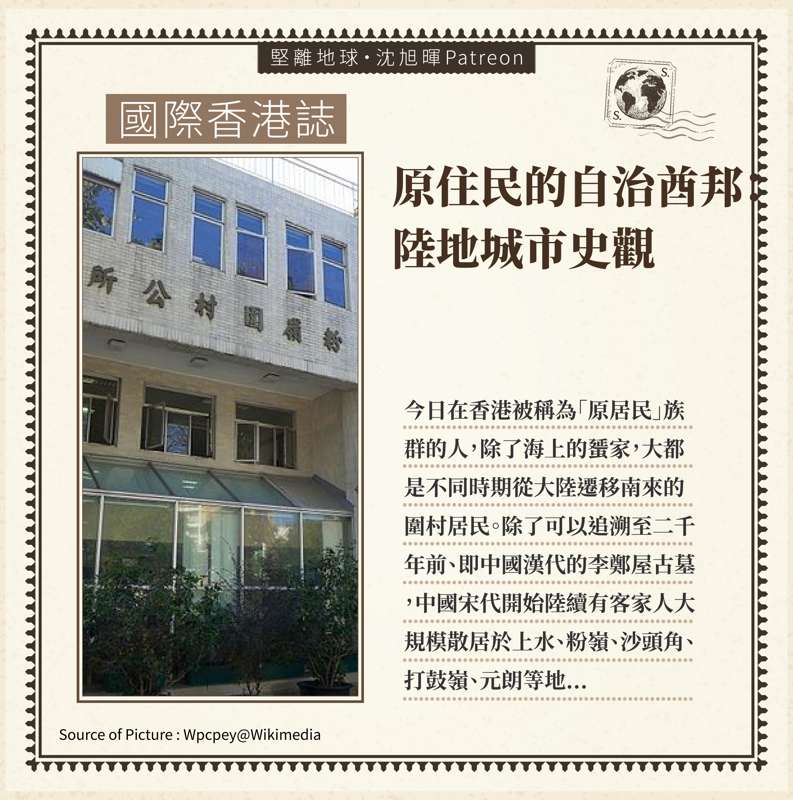【國際香港誌 12】原住民的自治酋邦:陸地城市史觀 (Patreon)
Content
根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,香港也可以從「陸地城市史觀」角度閱讀。這和「大中華史觀」最不同的是,以香港的陸上原住民為研究核心,並以陸地建立的早期鄉鎮開始為香港生命的主軸。
今日在香港被稱為「原居民」族群的人,除了海上的蜑家,大都是不同時期從大陸遷移南來的圍村居民。除了可以追溯至二千年前、即中國漢代的李鄭屋古墓,中國宋代開始陸續有客家人大規模散居於上水、粉嶺、沙頭角、打鼓嶺、元朗等地(均屬於1898年的「新界」租地範圍內)。[1] 這派史觀認為香港從不是中原朝廷、中土政權所能直接控制的,因為這些香港陸地族群以宗族為中心,建立圍村,以村落為單位實行自治,透過祭祖、辦學等促成內部維繫,產生自己的經濟活動,乃至有自己的鄉勇軍隊,而外部關係,同樣主要是宗族與宗族的合縱連橫。由於中原政權鞭長莫及,香港陸地上的居民「自古以來」習慣了自成一「國」,也衍生了「保家衛鄉」的傳統。英國租借新界時,他們由下而上的武裝和英軍進行了六日戰爭,正是他們「高度自治」的證明。而對英國殖民管治者而言,這種香港境內的陸地自治體,和在印度的大小土王、阿拉伯的大小酋長、馬來半島的大小蘇丹、乃至台灣原住民的大小股頭,本質上沒有分別。
這種自治體的形成,可以用社會學的角度來理解。美國漢學家施堅雅(George William Skinner) 的研究顯示,宗族乃中國傳統社會的基礎;[2] 而參考施堅雅的學生蕭鳳霞對南中國社會結構的研究,香港圍村的結構大概亦受此傳統影響,只是因為更邊陲,而更容易形成自己的體系。[3]「古代國家建設仰賴不流動的農業生產、和定點居住的農村人口,這可以解釋傳統的國家論述與文明制度,都表揚農業社會、而貶低游牧民族,更視之為漢文明禮教與蠻夷的最大分野。定居的農村人口較容易被管治,亦是政府主要稅收的對象。」[4] 由此可見,宗族圍村的出現,本來乃因應農業生產的需求,再逐漸形成自己的管制體系。以荃灣為例,原名為「淺灣園」的老圍村居民以農業為生,利用梯田種米種菜,同時亦從事養豬、砍柴、割草等謀生,再經由海壩作為貿易、運輸的中心地,這種模式符合施堅雅對傳統中國農村市場的描述。至於圍村與海上商業世界的腹地關係,則相對不為這一學派重視,焦點往往放在不同圍村之間市集的開放日期,作為他們的世界觀。[5]
這樣的自治體到今天依然存在,不過隨着都市化發展,難免淡薄了很多,令這個史觀要繼往開來,難免無以為繼。港英接管新界後,陸續有大量居民從四方八面遷入香港、包括新界地區在內,工業發展也逐漸取代原來的農業生產,一如其他類似社區,農業和宗族社會因為社會環境變遷而逐漸變質,不少青壯居民選擇外出打工,村屋和農田則改為放租,到後來位於市區的圍村均被清拆,村民也變成都市人。然而時至今日,這種香港陸地史觀依然有其他應用功能,例如香港學者羅貴祥以陸地「耕作村」相對於海上「海盜邦」為香港兩大組成體系,認為農地敘述的想像不必限於傳統,反而可以視作對抗港英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市場政策的力量。[6] 透過融入生態運動、有機耕作、食物自主與安全、環保意識、文化保育等不同理念,農地敘述也可以啟迪包含多元價值的本土主義,去重建本地糧食供應,從而減少對進口貨物的依賴。此外,不少香港原住民因為港英政府對歸化英籍的政策(或漏洞),集體移居英國或歐洲大陸、但依然與香港土地保持法律聯繫,構成了一個獨特群體,這也是香港全球脈絡的另類章節。
港英政府明白到香港原居民的特殊性和自治傳統,但也不希望這種傳統影響到在原有土地香港島、九龍半島的管治模式,因此早就引入「一地兩制」,以新界鄉紳組成的鄉議局傳承圍村的自治傳統,作為自治體的邦聯機構。而「原住民」概念的法律確立,同樣是源自鄉議局和港英殖民政府的糾紛:1972年,港英政府為了區別因應興建新市鎮而遷入的市民、以及原來的圍村居民,定義了「父系源自1898年時為香港新界認可鄉村的男性居民」為「原居民」,既是以特權籠絡圍村人,同時也是削減鄉議局對收地政策的影響力,避免其自治體得到不成比例的膨脹。[7]
[1] 王永偉。2018。族譜中的移民:淺析清中前期客家人在新界的分佈。惠州學院學報第38卷第4期。王錫琴。2017。香港客家宗族文化與傳承。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7年1月第一期。
[2] Skinner, William (施堅雅)。1991,《中國封建晚期城市研究》。吉林:吉林教育出版社。
[3] Siu, Helen. 1989. Agents and Victims of South China. 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.
[4] 羅貴祥。2016。從海盜邦到耕作村: 國家主權下香港的海岸與農地敘述。文化研究 第二十三期 2016年秋季。
[5] 江玉翠。2018。香港客家村落的轉變與延續: 以荃灣老圍為例。全球客家研究,2018 年 5 月 第 10 期,頁 209-234。
[6] 羅貴祥。2016。從海盜邦到耕作村: 國家主權下香港的海岸與農地敘述。文化研究 第二十三期 2016年秋季。
[7] 鄺智文。2018。從「新界人」到 「原居民」英治時期香港新界村民的身份建構。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五十二期 2018 年秋/冬季。